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作为弘扬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载体,抗战文学是鼓舞民族斗志的号角,也是反映民族解放时代的镜子,留下了真实、深刻、难以磨灭的历史记忆。为挖掘抗战文学思想价值,讲好抗战历史故事,弘扬伟大抗战精神,8月12日,上海抗战题材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上海作协举行。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表示,上海作为抗战时期的重要战场与文化阵地,涌现了许多值得书写的人物和故事。他强调,在新时代书写抗战历史,既要真实表达抗战历史的艰苦卓绝,也要展示同时代人的真实生活。在展现多层面的生活的同时,更要体现出作家自觉的历史责任和家国情怀。“作家应结合当代读者的阅读需求,用多元化的艺术手法将抗战精神的力量形象、生动、艺术地表现出来。”

上海抗战题材文学作品研讨会,上海作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秘书长毕胜主持。摄影:罗昕
抗战文学的表现边界
上海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马文运表示,上海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是中国抗战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近十年来,小白的《封锁》、吴海勇的《起来》、马伯庸的《大医》、高渊的《诺曼底公寓》、简平的《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路内的《山水》等抗战题材文学作品,既延续了海派现实主义的传统,又在叙事模式和艺术表现上不断革新,持续拓宽了抗战文学的表现边界。
《封锁》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公寓,居住于此的汉奸头目遇害身亡,一场封闭式恐怖调查在公寓居民中展开;《起来》以纪实文学的方式,记录了艰难岁月中《风云儿女》和《义勇军进行曲》的创作过程;《大医》以清末民初至抗战时期的中国为背景,讲述三位青年因共同加入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华山医院前身)而结缘的故事;《诺曼底公寓》以建筑为载体,以全新的空间叙事展现了属于老上海的战争与和平、痛苦与荣耀、光荣与梦想;《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以1943年上海一群流浪儿的生活与成长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山水》以普通司机的命运为主线,展现了抗战时期人性的复杂性。

上海题材的抗战文学作品
激活尘封的历史记忆
“抗战文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有很多东西可写的题材。”小白表示,在《封锁》里,他想讨论的是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品格有点瑕疵的普通人,如何一步步战胜自己、超越自己,展现极大的勇气,成为一个英雄。“如何守住一个人的底线,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不仅是抗战时代的问题,也是所有时代的问题。”
马伯庸也认为,抗战题材应该从多维度、多层次、全景式呈现。《大医》是从医学的角度出发,他即将于今年下半年出版的抗战题材新作则有关古籍保护。他提及自己曾收到一位抗战史研究者转交的项松茂后人的感谢信,感谢他的小说内容对他们的先辈做了一次追认。“我也会感到很欣慰。因为我希望我的小说不仅仅是虚构的文学作品,也能激活尘封于大家记忆里的东西。”
路内探讨了个体经验与书面资料的关系,强调两者应结合,以还原真实的历史细节。比如《山水》中“夜战肉搏摸帽子辨敌我”这一细节,最初源于路内的家族口述,但经过严谨的史料考证,才最终被他写入书中。
高渊表示,写《诺曼底公寓》,横坐标是抗战时代的家国情怀,竖坐标是上海的城市精神。“上海的城市精神,书中用一句话概括,‘英雄不问出处’。”高渊说,比如诺曼底公寓的设计师邬达克,来上海之前没有设计过任何一幢建筑,离开上海之后只在美国设计了一幢私人住宅。“他在上海留下一百多幢单体建筑。有人说,邬达克把他所有的才华留在了上海。我觉得更准确的描述是,上海为邬达克的才华提供了最大的舞台。”
“上海”还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
许多批评家也分享了他们对于抗战文学的理解。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孟繁华在回顾中国抗战题材文学创作史时,对比了中西方在书写战争历史方面的差异。他认为,中国作家在书写抗战历史时,应不仅聚焦于可见的战争的累累痕迹——破碎的山河、城市、乡村,而应更加关注战争对人内心世界和精神层面造成的隐形创伤。
在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吴俊看来,一般会把上海理解为一个地域名词,但对于“上海抗战题材”这个说法,其实“上海”还可以作为一个形容词,即具有上海特色的、上海性的抗战题材。“在中国近现代所有城市里,没有哪一座城市的红色底色能和它相比。上海就是一个以红色为底色的城市。”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赞赏《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中“轻盈化”处理历史的方式。他还从文化传承角度,强调文学作品在塑造中华民族精神方面的重要作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表示,一个民族的血性、智性,在危急时刻、封锁时代显露无疑。新一代作家要拿出自己最好的艺术感觉、文笔和智力,写出非脸谱化、非概念性的民族英雄,讲好动人的抗战故事。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家装公司,本文标题:《从上海文学,看如何讲好抗战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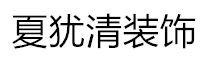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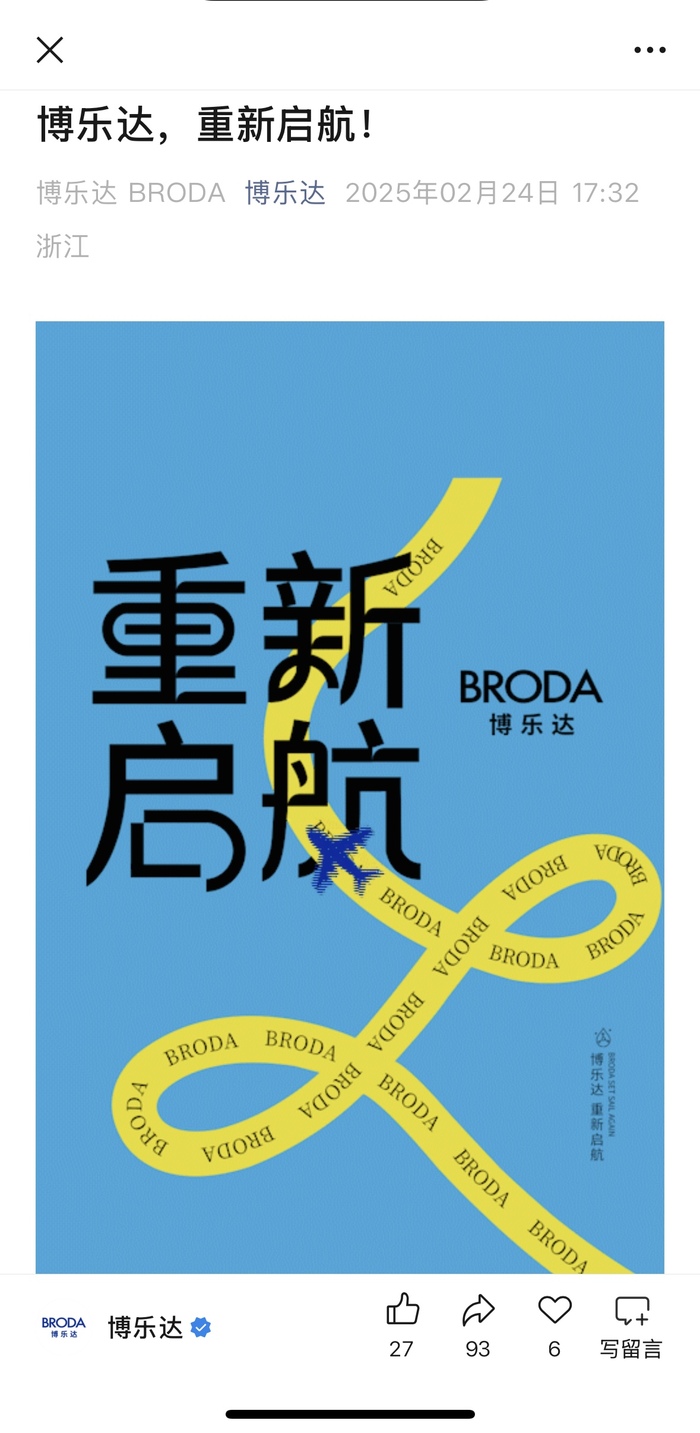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5
京ICP备2025104030号-5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