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沙正式陷入饥荒
一件尽管说起来很冷血但没人会意外的事情是,联合国专家宣布加沙城区已经正式出现大饥荒。这场饥荒毫无疑问是人为的,是以色列攻打、封锁加沙所导致的一系列人道主义危机的延续。随着近一段时间以来英国的主流媒体,特别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和《卫报》开始大力报道加沙局势,这场正在进行时的饥荒也得到了更多的曝光。当前,加沙局势日益恶化,该地区可谓是满目疮痍,整个地区死亡人数呈指数级上升。这场饥荒由联合国及合作伙伴组成的联盟开发、用于评估粮食状况的“综合粮食安全等级分类”(IPC)认定,该机构一般会把粮食危机状况分为五档,而最严重的第五档对应的即是饥荒。而它们也在近日公布,当前的加沙已经满足饥荒的三个关键标准,标志着这一人道主义危机的重大升级。

当地时间2025年8月21日,加沙地带汗尤尼斯,人们排队领取免费热餐。
在数据统计中,饥荒的标准是冷冰冰的——要正式宣布饥荒,必须满足严格的标准,包括至少20%的家庭面临极端粮食短缺、至少30%的儿童患有急性营养不良、每1万人中每天至少有两人死于“彻底的饥饿”等。自2004年以来,IPC仅宣布过四场饥荒,最近一次是在去年的苏丹。在针对加沙局势的报告中,IPC表示:“这场饥荒完全是人为造成的,也可以得到遏制和扭转。已经没有时间争论和犹豫,饥饿已经存在并迅速蔓延。任何人都不应再怀疑,而必须立刻展开大规模措施加以应对。但凡再拖几天,时机的延误都会导致饥荒相关死亡人数出现骇人增长。”报告还警告称,如果不立即停火,使人道主义援助能够抵达加沙地带、支援所有当地居民,并恢复基本的粮食供应以及卫生、营养和水资源服务,死亡人数还将呈指数级上升,而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在7月份的时候,IPC就警告说加沙部分地区正出现“饥荒情景”,但当时由于缺乏确凿数据尚未正式宣布饥荒状态的到来。
目前陷入饥荒的加沙城区及周边地区是加沙一带最大的居民聚集区,人口规模在50万到80万之间。但IPC的报告也指出,加沙地区中部的Deir al-Balah和南部的Khan Younis等地也可能在“未来数周内”陷入饥荒。可以看出,尽管饥荒的认定需要足够的数据来支撑,但数字和现实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时间差,IPC的专家也表示,目前他们采集到的数据不足以宣布加沙北部进入饥荒状态,但在当地进行援助的官员称,那里的情况反而可能是最严重的,并呼吁采取紧急措施,以开展全面的人道主义评估。有加沙当地的居民告知《卫报》记者,他们已经连续很长时间每天只能吃一顿饭,而且只能吃一些煮豆子,虽然有援助者救济他们大米和蔬菜,但长期挨饿的她已经吃不下蔬菜,一吃就会胃痛,而且他们也已经饿到没有力气去排队领取救济物资。
《卫报》称,加沙饥荒的宣布将加大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压力,要求其放松自战争爆发以来施加的物资管控措施。英国外交大臣大卫·拉米(David Lammy)谴责这场饥荒是“道德耻辱”。他在声明中表示:“加沙城及周边地区的饥荒得到确认,既令人恐惧又完全可以避免。以色列政府拒绝允许足够的援助进入加沙,才导致了这一人为的灾难。”然而,以色列当局否认了报告的结论,声称加沙没有饥荒,并称相关发现是“哈马斯的谎言,经由既得利益的组织包装传播”。内塔尼亚胡更表示,以军将在数周内对加沙城发起大规模新攻势。援助官员警告称,若加沙再遭大规模军事行动,其后果对平民将是灾难性的。
原本普遍认为由以色列支持成立的“加沙人道基金会”(GHF)会取代此前负责粮食分发的大量援助组织,但目前他们并未能向居民分发足够的食物。另一方面,联合国及其他组织也面临巨大的后勤障碍:由于法律秩序几近崩溃,抢劫等治安事件从不间断,而来自以色列方面持续的军事打击,加上刻意为之的行政限制与官僚程序,也在拖缓援助的效率,更别提加沙境内的基础设施早已广泛受损。根据IPC的报告,平民在试图获取食物援助时仍不断大规模遭到以军方杀害,另外,GHF执行的私有化粮食分发机制显然缺乏规划、执行与监管,IPC方面对此也已表示严重关切。
自2025年3月以来,以色列对进入加沙的物资实施了近三个月的全面封锁,使得当地局势迅速恶化。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下,以色列一度于5月底开始允许有限数量的物资运抵加沙。当局还引入了前文提到的GHF,作为一套新的粮食分配系统,不过GHF的四个食品分发站都设在军事区,巴勒斯坦人必须冒着生命危险且长途跋涉才能到达,而这四个分发站所取代的是原来联合国运作下位于居民社区内的400个分发点。这就意味着,巴勒斯坦人如果不想饿死,他们就得冒着生命危险去领取食物,这就逼着当地居民在饥饿和死亡之间做出抉择。事实上,如同IPC的报告提到的,几乎每天都有在GHF分发点的人们遭到枪击。据联合国统计,自5月底以来,GHF站点附近至少有994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害,其中一些人在试图获取援助时被杀害。联合国称,大多数遇难者是被以色列军队射杀的,BBC所采访的目击者和加沙的医护人员也证实了这一点。当然,以色列仍是一再否认这些指控。换句话说,当前加沙的饥荒状态是在以色列的监督制度下造就的。
而就在本周,以色列当局批准征召数万名预备役部队,准备入侵已经陷入饥荒的加沙城区。内塔尼亚胡表示,接管加沙地区是击败哈马斯、结束战争和遣返加沙地带以色列人质的最佳选择。此次入侵将迫使居住在加沙城及其周边地区的约100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以色列已通知医务人员和援助机构做好撤离该地区的准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粮食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多个联合国机构发表联合声明,对此次计划中的攻势表示担忧,称“这将给已经存在饥荒的平民带来进一步的灾难性后果”,因为许多生病和营养不良的儿童、老人和残疾人根本无法撤离。
看起来当下已经没有任何一股力量能够有效遏止以色列当局的行径,仅存的可能性或许在以色列国内——一些媒体注意到,以色列内部已经逐渐开始有声音质疑内塔尼亚胡政府有意夸大以军击毙的哈马斯成员数量。一方面,自2023年10月7日遭遇哈马斯袭击之后,以色列军方希望挽回他们在以色列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夸大的敌人死伤数会是振奋人心的战绩;但另一方面,这或许意味着这场战争仍缺乏明确清晰的战略规划。当然,这也只是对于他们要打击的敌人数据的纠缠,对于因战争和饥荒死去的平民数字,关怀是不存在的,反倒是“哈马斯的谎言”这个理由已经被设置成自动回复。
(参考资料从略)
右翼解构派与虚无主义者:“右翼虚无主义”的兴起
当进步主义在文化层面掌握主导权时,许多保守派并非仅仅以政策进行对抗,而是逐渐走向更为极端的“虚无主义”立场:既怀疑进步主义,也怀疑民主制度本身。近日,《纽约时报》发表了美国专栏作者与资深评论员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评论文章《右翼虚无主义的兴起》。布鲁克斯在文中提出:这种心态不仅在美国蔓延,也可以在西方社会里找到普遍回声。

大卫·布鲁克斯(David Brooks)
近年来的国际政治动向已然揭示,虚无主义不仅是哲学术语,而且正在成为一种切实的政治心理与社会动力。虚无主义可能出现在不同的政治光谱之中,以不同的文化面孔出现,但它们共同指向了对制度、价值和未来的信任丧失。在不同意义上的“信任流失”成为某种普遍经验的今天,对虚无主义政治趋势的思考或许能提供一面理解社会与个人的放大镜,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信任危机、政治极化、公共空间的瓦解等议题。
在文章开头,布鲁克斯写下了这样一个场景:“民主党的朋友们,让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想象一下,某天早上你醒来,发现你所有的媒体资源都出自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之手。你送孩子去上学,老师们却在宣扬某种形式的基督教民族主义。你打开体育频道和深夜喜剧节目,却发现每个人都在宣扬基督教民族主义。这有点像如今在西方成为保守派的感受——感觉自己被进步主义说教无休止的倾盆大雨浇透。在这种情况下你会怎么做?嗯,至少一开始,你可能会咬紧牙关,默默承受,但心中怒火中烧。”
布鲁克斯提到的“基督教民族主义”(Christian Nationalism)是近年来在美国等国家被广泛讨论的一个概念。它并非单纯的宗教信仰,而是一种把特定宗教身份与民族、国家身份强行绑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其主张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与文化应当明确以“基督教价值”为基础,认为美国在根本上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是推动宗教与国家的高度结合,把基督教世界观作为公共政策的依据,排斥世俗主义和多元信仰。
作者让自由派读者想象生活在一个完全由“基督教民族主义”主导的舆论和文化环境中,以帮助他们理解许多保守派在当下感受到的“被浸透在进步主义话语里”的压迫感。布鲁克斯此文的核心观点可以概括为:当代西方社会的进步主义话语占据文化主导地位,这导致许多保守派和普通民众感到被压抑或被边缘化,这一状况激发了两种不同形式的反应——一种是克里斯托夫·鲁福式的右翼解构主义(Christopher Rufo-style dismantling),另一种则是更为激进的右翼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不仅是对进步主义的反击,更是一种彻底丧失信仰与意义感的文化现象,最终可能对社会和民主制度造成严重威胁。
出生于1984年的鲁福是美国激进保守派活动家,其所代表的右翼解构派试图解构“D.E.I.”(“多元、公平、包容”)和其他文化进步事业。在2024年,鲁福与美国极右翼人士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进行了一系列辩论,其间,鲁福强调了自己并非保守派而是激进派:“我想要摧毁现状,而非维护现状。”(鲁福和亚文的辩论内容发布于《IM-1776》杂志。)布鲁克斯认为,鲁福体现了旧式保守主义与特朗普主义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前者认为,自己是在保护某种文化、思想和政治传统免受后现代主义的冲击。而在后者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是值得保留的。右翼解构派并非“守护传统”,而是激进地反建制。
根据布鲁克斯的说法,亚文实则是当下右翼虚无主义者的一个代表。这种虚无主义以“进步思想是错误的”为前提,然后得出结论:所有思想都是错误的。持这种“亚文式虚无主义”(Curtis Yarvin-style nihilism)立场的人更极端地认为,整个民主制度和文明结构都是虚假的,必须彻底摧毁,即使没有替代方案。
因此,表面上看,右翼解构派和右翼虚无主义者都表现出某种“破坏性姿态”,但二者在破坏的目标、程度和背后的逻辑上存在显著差异。我们可以认为,右翼解构主义针对的对象主要是进步主义的制度化成果,例如“D.E.I.”、高校和企业里的多元文化培训等。其对抗逻辑在于,认为这些制度代表着后现代霸权对传统文化的侵蚀,因此要“拆掉”它们。因此,其运动的目标是通过拆解这些“进步”的制度,恢复或重建某种“正常秩序”。右翼解构主义的“破坏”可被理解为一种策略性破坏,虽然激进,但它仍然在政治博弈的框架之内。
相较之下,右翼虚无主义不仅针对进步主义项目,而是质疑整个制度本身,例如民主、宪政、现代文明价值等等。其对抗逻辑认为所有的现存结构都是虚假或腐朽的,而唯一的选择便是彻底摧毁它们,“让一切燃烧”。它的目标无所谓“重建”或“重构”,甚至不要求替代方案的存在,破坏或毁灭本身就是终点。右翼虚无主义的“破坏”是一种彻底的破坏,它超出了保守主义/政治改革等框架,转向了纯粹的否定与虚无。
因此,对于右翼解构主义来说,“破坏”依然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削弱进步主义霸权,为另一套秩序腾出空间。而对于右翼虚无主义而言,或许“破坏”即是目的,因为它认为没有任何秩序值得保存或重建。
实际上,“右翼虚无主义”的相关议题近年来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讨论。
例如,2022年,Discourse杂志刊载了Russ Greene的《虚无主义已占领美国政治》。作者认为,新右派的成功是美国背离自由民主、走向虚无主义的最新证据。当代美国政治正经历一种向虚无主义滑落的趋势——信念不再关注制度本身,而是“赢”本身。同时,他也提出了阻止虚无主义浪潮所必须回应的问题: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虚无主义者反对的是共产主义所提供的未来愿景,那么现代的对应愿景是什么?今天的虚无主义者反对的是什么样的未来愿景?而另一种愿景又是什么?
在2021年发表于《激进哲学评论》(Radical Philosophy Review)的论文《另类右翼的宣传与虚无主义》(Propaganda and the Nihilism of the Alt-Right)中,作者Cory Wimberly分析了作为网络亚文化的另类右翼的宣传技术谱系,指出其幽默、仇恨与暴力的结合如何孕育出虚无主义倾向,并认为基于阶级的左翼政治是对抗另类右翼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年1月,《卫报》文章《“反动的虚无主义”:右翼运动如何努力终结美国民主》介绍了新书《金钱、谎言和上帝:摧毁美国民主的运动内幕》(Money, Lies and God: Inside the Movement to Destroy American Democracy)。此书聚焦于一个由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亿万富豪和保守派意识形态者组成的反民主运动,作者斯图尔特(Katherine Stewart)认为该运动通过财富、谎言与宗教权力联手,推动了一种“反动的虚无主义”。
2024年,《大西洋月刊》也刊载了《需要混乱的美国人:他们正在拥抱虚无主义并颠覆政治》一文,作者汤普森(Derek Thompson)指出,当下的网络阴谋论者对阴谋论的传播并非为了伤害政治对手,而只是为了制造混乱。不同切入点的研究与关于当代虚无主义政治的不同界定,呈现了“右翼虚无主义”的复杂面貌。
布鲁克斯指出,当前,虚无主义正在美国扩散。在部分支持特朗普的社区,很多人已经对“有限改革”和鲁福式方法失去信心,转向了彻底的虚无主义立场。弗吉尼亚大学社会学家詹姆斯·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在2024年发表于《刺猬评论》(The Hedgehog Review)的文章中指出,“虚无主义文化的定义是毁灭的冲动,是权力的意志。而现如今,这个定义描述了美利坚民族。”布鲁克斯则在新文中转引了一位美国年轻女士的话:“区别在于,在你们那一代,你们有信仰,而在我们这一代,我们什么也没有。”
那么,右翼虚无主义的崛起有何后果?按照布鲁克斯的观点,虚无主义的本质不仅是对制度的不信任,还包括对宗教、社会信任、职业道路等传统价值的信心的丧失。他将当前的这种趋势与19世纪俄国虚无主义、战后德国和中欧的虚无主义浪潮作比,认为其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的激烈动荡。根据盖洛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人们对美国主要机构的信任度目前已接近46年来的最低点。
我们看到,在美国,右翼虚无主义对于青少年和Z世代的影响已经显现。
今年5月发表于Just Security论坛的文章《虚无主义暴力极端主义:美国反恐的伟大进步》提到,在对于威斯康星州少年尼基塔·卡萨普的审判中,美国联邦调查局使用了一个新词来形容卡萨普——“虚无主义暴力极端分子”(Nihilistic Violent Extremist)。17岁的卡萨普以“获取必要的经济来源和自主权”为由谋杀了父母,并想暗杀特朗普总统。FBI将“虚无主义暴力极端分子”定义为:“在美国境内外从事犯罪行为的个人,其目的是实现政治、社会或宗教目标,这些目标主要源于对整个社会的仇恨,并希望通过制造无差别的混乱、破坏和社会不稳定来导致社会崩溃。”
而在高等教育的空间里,受到“觉醒”运动影响的学生们则可能为了符合主流的进步观念而不得不公开撒谎,即使自己在私底下对某些“进步”观点持质疑或否定态度。
美国西北大学临床和应用心理学研究员Forest Romm和Kevin Waldman在2023年至2025年间,对来自西北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本科生进行了1452次保密访谈。他们的研究发现,有高达88%的学生表示,为了在学业或社交方面取得成功,自己假装得比实际上更为“进步”;有超过80%的学生表示,为了迎合教授的进步主义观点,他们会提交与自己真实观点不符的作业。
《国会山报》在8月12日刊登了Romm和Waldman的文章《表演性的道德炫耀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的威胁》。作者提出,这项研究旨在关注的问题是:“当信念被对正统观念(orthodoxy)的坚持所取代时,身份认同的形成会发生什么变化?”他们认为,上述88%的学生“并非愤世嫉俗,而是适应性强。在校园环境中,成绩、领导力和同伴归属感往往取决于能否丝滑地展现美德,而年轻人很快就学会了如何演练那些安全的道德规范。”但是,这种“丝滑的适应”的结果“并非信念,而是顺从。而在这种顺从背后,(他们)丢失了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
在电影《蝙蝠侠:黑暗骑士》中有一句著名台词——“有些人只想看着世界燃烧。”(Some men just want to watch the world burn.)这句话精准描绘了布鲁克斯笔下“右翼虚无主义者”的画像。通常被定位为“温和保守派”的大卫·布鲁克斯近年来尤其关注意义危机的问题,他强调“社会信任”“公共美德”“共同体价值”的缺失是美国困境的根源,主张超越个人主义、寻找集体归属和精神价值。通过对“右翼解构派”和“右翼虚无主义者”的区分,他实际上想指出“新右翼”已经不再是保守,而是激进乃至虚无,并将传统保守主义与特朗普主义、极端主义划清界限。
在《纽约时报》此文的结尾处,布鲁克斯写道:“一个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年轻男性,正在重返教堂。……在英国,根据一项研究,2018年,只有4%的18岁至24岁年轻人去教堂,但到2024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6%。”这一最终落脚于期待“信仰回归”的处理,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本人某种“回归更稳健的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家装公司,本文标题:《澎湃思想周报|加沙正式陷入饥荒;“右翼虚无主义”的兴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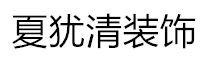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5
京ICP备2025104030号-5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