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正常细胞的表面像一个修剪整齐的花园,那么癌细胞的表面则像一个唾液酸过度生长的“热带丛林”。这片“丛林”正是癌细胞的伪装。新型药物分子能够保证“除草机”仅对癌细胞进行修剪,而不会伤到正常细胞。
·双功能唾液酸酶融合蛋白疗法计划在明年启动首个人体临床试验。
近年来,免疫疗法的突破为许多癌症患者带来了希望。科学家将人体免疫细胞进行改造,让其能够识别“伪装”成正常细胞的癌细胞,从而激活免疫系统对抗癌症。
科学家们正在探索更多癌细胞逃脱免疫细胞“追杀”的机制。8月25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第十二期“浦江科学大师讲坛”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卡罗琳·贝尔托齐(Carolyn Ruth Bertozzi)教授在题为“甜蜜的复仇:癌症免疫治疗中的‘去糖’行动”的演讲中,介绍了藏在癌细胞“糖衣”中的伪装机制和药物策略。

卡罗琳·贝尔托齐在“浦江科学大师讲坛”上介绍藏在癌细胞“糖衣”中的伪装机制和药物策略。图片由主办方提供
贝尔托齐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作为生物正交化学领域的开创者,她因该领域的贡献获得2022年诺贝尔化学奖。在演讲交流环节,她与现场听众交流了作为科学家的成长过程以及对科研工作的看法。
细胞的“糖衣身份证”
“我们所有的细胞表面都覆盖着复杂的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贝尔托齐回忆起自己在1986年作为一名本科生时,曾好奇地问教授这层“糖衣”的作用,当时得到的答案是“可能像M&M巧克力豆外壳一样起保护作用”。
后来科学家们才发现,这层糖衣更像是细胞的“身份证”,编码着关键的生物信息。免疫细胞可以通过“品尝”这层糖衣来判断细胞的“好坏”,从而决定是否攻击。
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人类的血型。“决定你是A型、B型还是O型血的,正是你红细胞表面糖链末端的细微结构差异。”贝尔托齐解释道。免疫系统能精准识别这些差异,错误的输血会引发致命的免疫攻击,这证明了免疫系统对细胞“糖衣”的高度敏感。
大约在50年前,科学家就观察到癌细胞的“糖衣”与正常细胞不同。贝尔托齐的团队发现,许多癌细胞表面会异常地大量生长一种名为“唾液酸”(sialic acid)的糖分子。如果说正常细胞的表面像一个修剪整齐的花园,那么癌细胞的表面则像一个唾液酸过度生长的“热带丛林”。
这片“丛林”正是癌细胞的伪装。它会与免疫细胞表面的抑制性受体Siglec结合,相当于向免疫细胞传递了一个“我是自己人,别攻击我”的错误信号,从而让免疫细胞“陷入沉睡”,放任癌细胞生长和扩散。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即使使用了其它唤醒T细胞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许多患者的免疫系统依然对肿瘤视而不见。
分子“除草机”
既然找到了问题所在,贝尔托齐团队的思路变得清晰:如果能把癌细胞表面的“唾液酸丛林”清理干净,免疫系统不就能重新发现“敌人”了吗?
为此,他们设计了一种新型药物分子,贝尔托齐将其形象地称为“分子除草机”。这种药物是一个巧妙的嵌合体:它由一个能特异性识别癌细胞的“导航系统”(单克隆抗体),和一个能切除唾液酸的“切割刀片”(唾液酸酶)构成。这种构造能够保证“除草机”仅对癌细胞进行修剪,而不会伤到正常细胞。
如何将“导航系统”和“切割刀片”精确地连接在一起?这正是贝尔托齐获得诺贝尔奖的技术——生物正交化学(Bioorthogonal Chemistry)大显身手的地方。通过“点击化学”反应,研究人员可以在不干扰细胞内复杂生命过程的情况下,像订书机一样“咔嗒”一声,将抗体和酶稳定地连接起来。
“这个疗法已在癌症动物模型以及相关的自身免疫疾病项目中验证,我们还在大型动物(比如猴子)中测试了这些候选药物的安全性。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进行首次人体临床试验,这是最终的考验。”贝尔托齐透露,她的团队成立了Palleon制药公司,并与上海的复宏汉霖(Henlius)达成合作,共同开发双功能唾液酸酶融合蛋白疗法,计划明年启动首个人体临床试验。
责任、开放与多元
贝尔托齐在演讲中提到,她原先的目标是进入医学院,但在医学预科的化学课堂上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开始了一生的求索。贝尔托齐不仅在科学领域中获得了杰出成就,也通过导师、技术顾问、企业创始人、杂志创办者等身份推动科学共同体的发展。
包括Palleon公司在内,贝尔托齐已经共同创立了多家企业,帮助她的实验室中产生的成果走向临床。“实在是太忙了,很花时间。”当被问及如何平衡科研与创业时,她向澎湃科技坦言。贝尔托齐说,这些公司的创立基本都是她学生的主意,“当一个学生对自己的博士课题充满信心,并希望将它变成一家公司时,我必须帮助他们。”
在贝尔托齐看来,导师与学生之间不仅是责任与服从,也有开放和个性,这种合作关系能帮助人们在没有标准答案的科学前沿探索中有所收获。
她分享了与她共同荣获 2022 年诺贝尔化学奖的丹麦化学家摩顿・梅尔达尔(Morten Meldal)的科研故事。某次实验中,梅尔达尔指导的研究生得到的产物与预期不符,看似是一次操作失误。研究生们详细记录了反应的主产物与副产物,导师梅尔达尔听取汇报后,建议他们重复实验。最终,研究生发现了一种全新的反应模式。
贝尔托齐认为,研究生实事求是的严谨态度是找到新发现的关键;而梅尔达尔开放包容的态度,为他们自由开展研究提供了空间。
贝尔托齐的实验室里有化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甚至还有拥有创意写作硕士学位的学生。“我并不希望我所有的博士生都来自哈佛,”贝尔托齐强调,“一个多元化的团队能带来更多想法。”她举例道,一位来自非洲布隆迪的学生让她深刻理解了结核病诊断在当地面临的社会污名问题,从而调整了诊断技术研发的方向。“这种视角,是我在加州无法获得的。”
开放与多元的理念也延伸到了贝尔托齐在学术出版领域的工作。作为《ACS Central Science》期刊的主编,她推动该刊成为美国化学会第一本完全开放获取的期刊——读者免费阅读,作者也免费发表。“这意味着全世界任何人,无论是在资源有限的大学,甚至是一名高中生,都可以无障碍地获取最前沿的科学知识。”
幸运的时代
当被问及个人认同与科研事业的关系时,贝尔托齐坦言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在她开启职业生涯的1980年代,美国社会正变得愈加开放和包容,使得她的个人身份没有成为追求科学事业的阻碍。
“如果我早出生十年,这些机会可能就不会属于我。”贝尔托齐说。
这份“幸运”也离不开家庭的庇护。她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当时“科学不适合女孩”的观念在美国社会依然普遍存在。但她的父亲——一位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坚决地否定了这种偏见。他为三个女儿创造了一个充满鼓励和支持的环境,让她们可以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兴趣,从未因性别而受到任何限制。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应该会有更多的父亲像我的父亲那样想。如果把女性排除在科学之外,那等于排除了50%人口——这些人的头脑中本应该有多少好点子!”贝尔托齐告诉记者。
时代不仅有限制,也有潮流,可能会影响个人的选择。一位复旦大学的老师无不担心地指出,随着国内科研水平的提高,竞争变得越来越激烈,很多学生对于进入科学领域充满犹豫。对此,贝尔托齐认为,要有勇气去直接面对内心和真实的世界。
“比如现在计算机专业很火,MIT(麻省理工学院)可能有50%的学生都在搞AI。”她说,“但是大家其实知道,这些技术仅仅是工具。它或许能告诉你蛋白质如何折叠,甚至在未来直接告诉你使用哪些蛋白质可以成药,但前提是你得把它真正做出来,然后放到实验室里去研究。”
虽然个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贝尔托齐也提到,只有打好基本功,才能一窥某个领域真正的风景。
“我曾经对化学一点也不感兴趣。高中化学课结束时,我心里长舒一口气,想着终于结束了!后来读医学预科时,也是因为必修才选了化学课。”面对一名中学生对化学应试教育的抱怨,贝尔托齐笑道。在哈佛读本科期间,她甚至还在一支名为“厌学”(Bored of Education)的校园重金属乐队担任键盘手。
贝尔托齐说,她后来才意识到,正是这些枯燥的练习,“如同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一样”,让未来的化学家像运动员那样“长”出能够支撑创造性工作的“肌肉”,才能在科研的赛场中酣畅淋漓地竞技,体验这一活动的美感与意义。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家装公司,本文标题:《诺奖得主贝尔托齐:癌细胞“糖衣”的伪装机制和药物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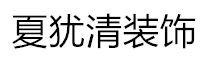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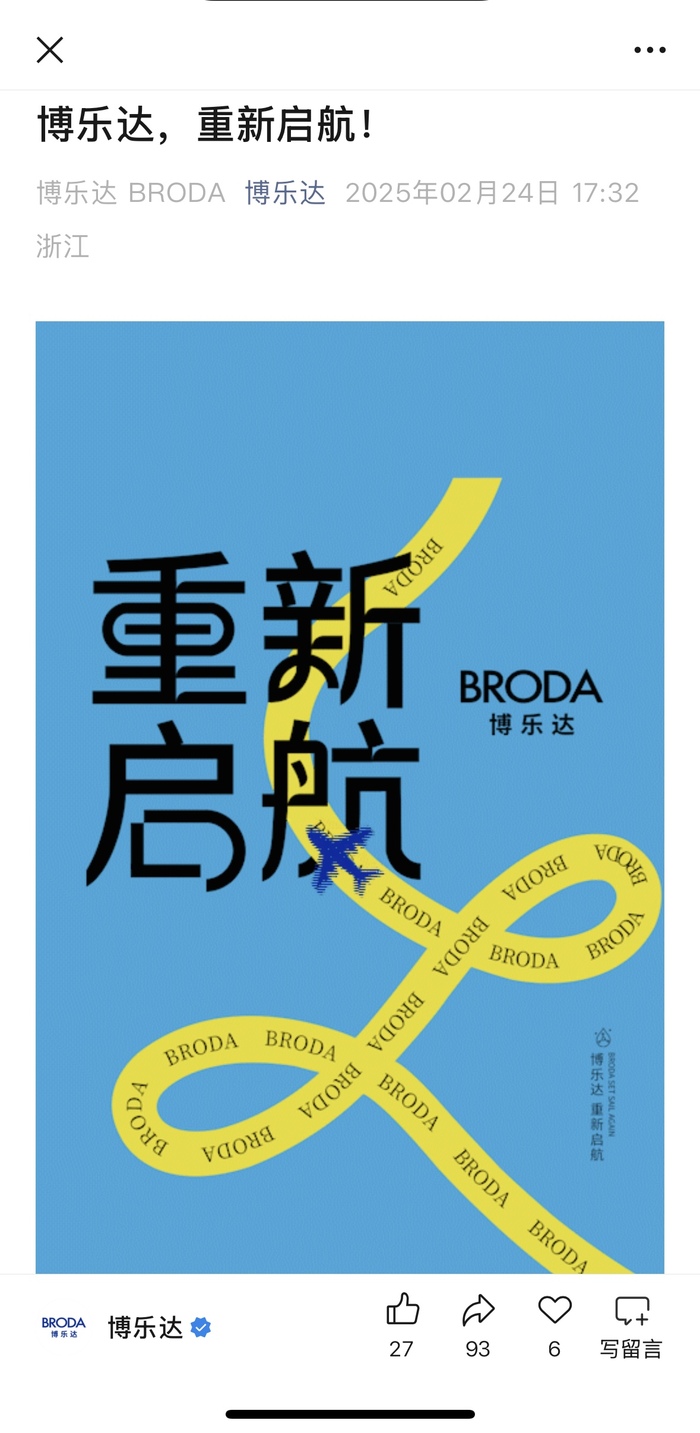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5
京ICP备2025104030号-5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