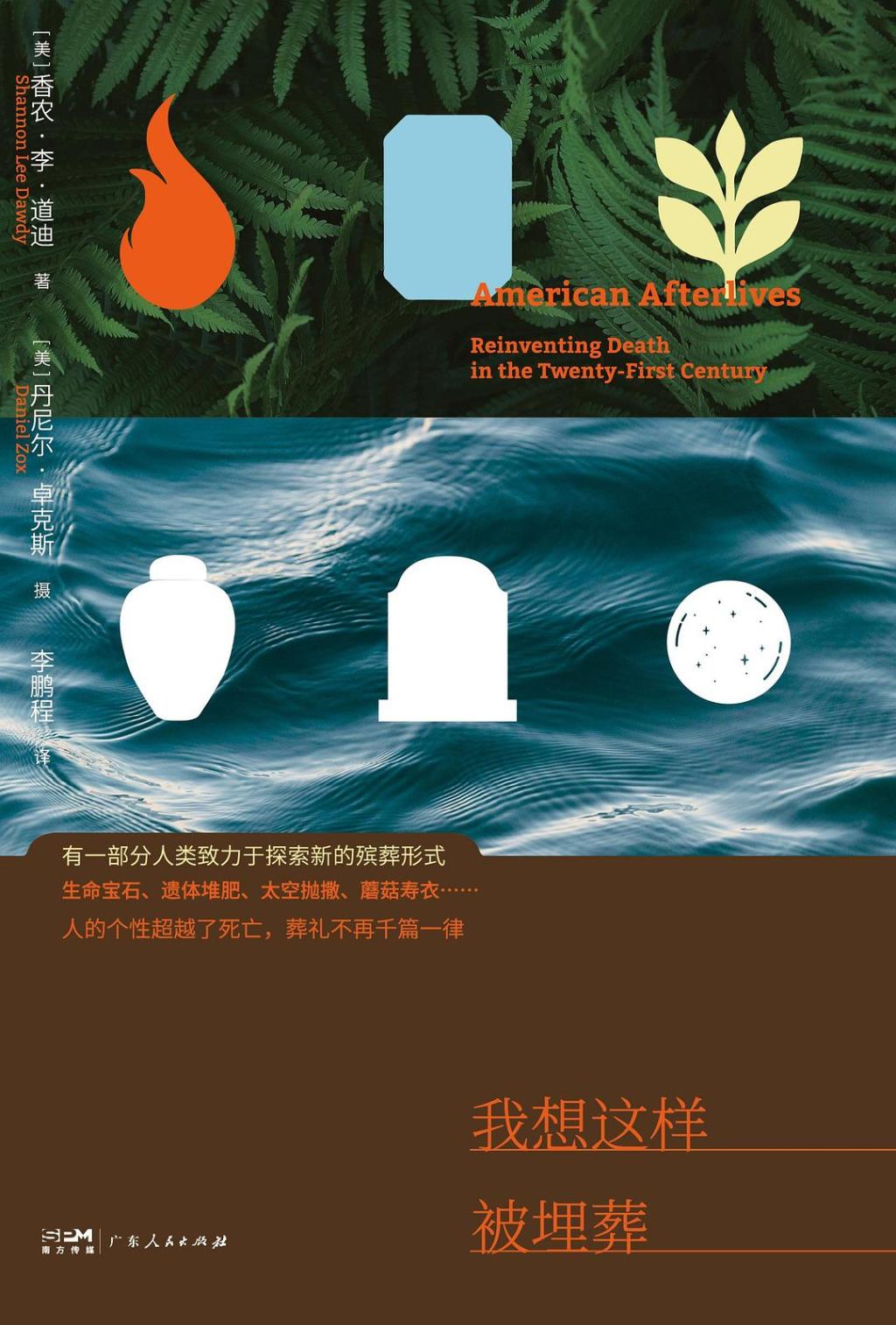
《我想这样被埋葬》,[美]香农·李·道迪 著/ [美] 丹尼尔·卓克斯摄,李鹏程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乐府文化,2025年1月版,339页,68.00元
从2015年到2020年,美国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香农·李·道迪和她的搭档、纪录片导演丹尼尔·卓克斯走遍了美国各地,从佛蒙特到加利福尼亚,从伊利诺伊到亚拉巴马,从殡仪馆、公墓到各种殡葬产品创意公司,不辞辛劳地寻访殡葬师、墓地老板、殡葬创业者和临终导乐,了解后者亲眼目睹或正在推动的美国殡葬业正在发生着哪些变化。香农和她的导演搭档试图记录下二十一世纪的前二十年美国日新月异的殡葬习俗,进而探究“应对死亡的种种变化所折射出的美国人在当下的历史节点秉持着怎样的信仰和价值观念”。
在经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人员访谈后,香农和丹尼尔最后出色地拍摄出了一部长达二十一分钟的纪录片《我喜欢土》。在此基础上,香农又于2021年出版了一部关于美国殡葬业的人类学著作。如果按照中文直译,这本书应当被翻译为《美国人的身后世界:21世纪的死亡重塑》。然而,颇为有趣的是,译者将其翻译成了《我喜欢这样被埋葬》。在书中,香农具体而生动地呈现了当下美国殡葬习俗正在发生的种种新变化,探讨了其与美国人对身体、个人以及宇宙运行方式的信仰和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二十世纪标准化的“美国式死亡”
法国历史学家菲利普·阿里耶斯在其蜚声学界的死亡史著作中,将中世纪以来信仰基督教的欧洲人对待死亡的态度划分为五种模式。其中,最后一种模式是“看不见的死亡”。二十世纪的欧洲人多数在医院中离世,遗体由殡仪馆的工作人员接走处理。死亡,被科学和工业主宰。原本人们时常见到的死亡,自此在公共生活中消失了。菲利普·阿里耶斯认为,二十世纪的美国就是这种模式的极端个案。美国人死亡后,被迅速“藏”进殡仪馆或郊区公墓中。这体现着美国人对于死亡的普遍恐惧,是一种典型的“死亡否认”。菲利普·阿里耶斯进而断言,美国俨然就是一个“驱逐了死亡的社会”([法]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对死亡的人》下卷,王振亚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444页)。
对于菲利普·阿里耶斯划分的关于欧洲人死亡态度的五种模式,香农并不满意,认为这只是历史学家坐在书桌前整理史料而得出的理想结论。言外之意,无疑是在批评菲利普·阿里耶斯的研究缺乏对现实的深入探究。与此同时,对于菲利普·阿里耶斯关于美国葬礼的观点,香农也并不能完全认同。不过,香农也不得不承认,二十世纪美国的殡葬习俗确实有着相当独特之处。显然,只有对二十世纪美国的殡葬习俗略加考察,才能对二十一世纪殡葬习俗的新变化有所了解。
首先,美国人对遗容瞻仰有着一种固执的迷恋。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遗容瞻仰构成了美国式葬礼中神圣的一环。香农指出,这在其他国家,是很少见的。在现实生活中,除了穆斯林和犹太教徒外,佛教徒、印度教徒与基督徒也多数期望这样做。为何美国人对遗体瞻仰如此热衷?研究死亡的学者和殡葬师给出了种种解释。其中,一种流行较广的观点认为,这要追溯到美国建国之初基督教福音派的天堂观念。福音派认为,在守灵或下葬前,生者需要瞻仰遗容并牢记逝者容貌,以便将来在天堂相聚。这也可以用来解释,当时有财力的家庭何以会为逝者制作死亡面具、绘制肖像画或拍摄照片。这一观点,与菲利普·阿里耶斯关于浪漫主义时代欧洲人对死亡态度的模式总结倒是颇为相近。然而,在香农看来,这些观点都不足以“令人信服”。
美国人对遗容瞻仰的执念,构成了遗体防腐被推广使用的基础。现代动脉防腐技术发明于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原本主要用于医学解剖、保存遗体之用。其操作方法是通过在遗体的动脉处切口,然后由导管泵入防腐剂,同时导出血液。遗体防腐技术被应用于美国人的殡葬活动,要追溯到南北战争时期。据史学家研究,在持续四年的南北战争中,大约有六十二万名美国士兵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美国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美墨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中美国死亡士兵人数的总和([美]德鲁·吉尔平·福斯特:《这受难的国度:死亡与美国内战》,孙宏哲、张聚国译,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序言”,003页)。为了符合善终理念,阵亡士兵的家属们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将他们的遗体运回家中。为此,野战医院不得不采取简单的防腐措施,同时对运送遗体的车辆也做了冷冻处理。通过遗体防腐处理的遗体,满足了美国人瞻仰遗容的需要。于是,遗体防腐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开始兴起。
香农认为,南北战争是美国殡葬习俗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其影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在南北战争以前,遗体处理主要由有着经验的家庭妇女或左邻右舍帮忙料理,有着相当的私密性。然而在南北战争以后,男性专业人士在殡葬事务中开始发挥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市中专门从事殡仪服务的殡仪馆大量涌现。美国殡葬业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进程,从此迅速发展。家庭在殡葬事务中的重要性,则逐渐降低。到了十九世纪末,殡葬师(mortician)的职业称谓出现。香农专门对“mortician”一词进行了解读,指出“ician”为“physician”(专业医师)一词的后缀。说明这个词在被创造之始,就是希望从事该类行业的人能够被作为特殊医师看待。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殡葬业的专业化已然完成。在这一时期,各种殡葬行业团体、执照制度、法律法规等已一应俱全,标志着美国的殡葬业完全被商业化、标准化。遗容瞻仰和遗体防腐,几乎成了殡葬活动的标配。英国记者杰西卡·米特武德在她那本批判美国殡葬业的标志性畅销书中指出,美国人的这种殡葬“传统”,到了20世纪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新型神话”([英]杰西卡·米特武德:《美国式死亡》,李雪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版,15页)。据美国殡葬协会(NFDA)的统计,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逝者采取了遗体防腐处理。遗容瞻仰、遗体防腐和水泥套棺,成为了二十一世纪以前美国人的标准的、“行将就木”的“美国式葬礼”。
那么,如何来理解这一标准的“美国式葬礼”?香农倾向于认同这样的一种观点。即,遗体对于亲属有着情感疗愈的作用。当亲属在看到或抚摸遗体时,内心的悲伤情绪会得到一定程度的纾解。否则,家属的悲伤情绪无所依托,不仅得不到释放,反而还会加重。因此,遗体在葬礼中是作为一种“神圣物”而存在的。人的死亡,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生物性死亡,一个是社会性死亡。香农强调,防腐技术显然是“延长了逝者的生物性死亡和社会性死亡的临界阶段”。美国人对瞻仰遗容的坚持,并不是逃避死亡,而是为了和死者“好好道个别”。因此菲利普·阿里耶斯等人关于美国普遍存在的“死亡否认”的观点,在香农看来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对于美国葬礼中遗容瞻仰和遗体防腐的标准搭配,香农认为还有着更深厚的政治文化功能。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人种、民族和宗教相当多元的移民国家。然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对遗容瞻仰和遗体防腐的普遍接受,说明了美国的殡葬是作为一种“美国公民宗教”的组成部分发展起来的,体现着美国人的一种国家层面的“礼仪规范”。换句话说,这也是美国人之所以为美国人的原因。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二、二十一世纪以来日趋“个性”的美国式葬礼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尽管遗容瞻仰、遗体防腐依然在人们的治丧活动中占据着相当比例,但是美国的殡葬习俗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在发生着显著变化。对于这一“分崩离析”和“欣欣向荣”同时发生的领域,香农并不想以“家庭相册”的形式、巨细靡遗地一一呈现。具有考古学专业背景的她,更加希望通过考察殡葬习俗中“新生的器物”和“新兴的实践”,来反映新世纪以来美国殡葬习俗的剧烈变迁。
首先,美国殡葬习俗的显著变化,体现在绿色殡葬在民间的蓬勃发展上。香农发现,从卡莱罗纳到新英格兰地区,再到整个西海岸,一场更为广泛的绿色殡葬运动正在美国民众中间兴起。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美国人对遗体防腐正在失去兴趣。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防腐液无论通过动脉还是静脉进入人体,对于逝者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即便现在的防腐液已不再是副作用很强的福尔马林,依然会对逝者的皮肤产生损害。不仅如此,遗体经防腐处理被埋葬后,还会在墓穴中累积有害物质,从而对土壤、水产生不利影响。
在位于加州塞瓦斯托波尔市的芬伍德公墓,香农看到了一处非常“纯粹”的生态墓区。该墓区在安葬遗体时,不进行任何防腐处理,也不用含金属或塑料的标记物、殡葬用具和陪葬品。仅用可降解的木制棺材、柳条棺材或天然纤维裹尸布,盛殓遗体。为了减少碳足迹,挖掘墓坑也仅限人工挖掘。在墓表上,不使用任何人工雕饰的石材,只是用野外的石块堆积作为标识。在这片生态墓区内野草丛生,狐狸、郊狼、山猫和鹿等野生动物自由出没。有一天早上,公墓员工甚至发现一只美洲狮,正趴在一处墓碑旁懒洋洋地晒着太阳。
在北加州和其他一些地区,香农还发现,有一些公司正在推广经营“善地森林”的概念与业务。所谓的“善地森林”,实质上是一种“保护性骨灰分撒林”。即,殡葬服务公司购买老龄林(如生命力为数百年的红杉林),然后以国家公园为范本打造成为纪念公园。客户购买将骨灰撒在树下的使用权,价格视树种、树龄、位置以及客户是否单独使用一棵树而定。在树的底部,仅仅安装一块朴素的、印有购买纪念权人姓名的铜牌。为了降低骨灰分撒对当地生态的危害,服务公司还会聘请林业专家,根据当地土壤和树木生长需要制定出不同的保护方案。“善地森林”业务在美国,颇受喜爱大自然人士的欢迎。这一群体中,很多人表示死后“想成为一棵树”。
在一些学者看来,火化十九世纪以来在美国的不断推广,主要是由于这一处置方式经济实惠和携带方便。然而,香农指出其原因要复杂得多。一方面,火化的推广与美国城市化导致的人口过密和土地紧缺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国家公共卫生的启动和倡导分不开。此外,还与反天主教人士、无神论者、唯灵论者等分别从各自的立场选择火化这种方式有关。正是在这些因素的交相作用下,火化成为了二十世纪美国人处置遗体的重要方式之一。到了1995年,美国的火化率已然达到了百分之二十一。一些州的火化率则达到了百分之五十,甚至于更多([英]杰西卡·米特武德:《美国式死亡》,111页)。据美国火化协会统计,火化后的骨灰,三分之一被安葬在了公墓,三分之一被抛洒在各个地方,三分之一被家属带回了家中。
进入二十一世纪,与火化率不断提高相伴随的,是多元化、个性化的骨灰创意业务正在大量涌现。比如,一项制作包含骨灰在内的“纪念性物品”运动,正在美国兴起。这些“纪念性物品”,包括“玻璃纪念”“生命宝石”和“骨灰画像”等多种形式。相关纪念物品的制作,一般要先经过净化、减除成分,然后再制作成新的物品。香农认为,纪念性物品对于遗属而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念想”,而是为了在生者的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借助这些纪念性物品,生者和逝者之间的联系可以延续下去。
在俄亥俄州的一家名为“玻璃纪念”的艺术玻璃工作室,香农看到了一个外形被做成了破碎海浪形状的玻璃制品。在玻璃制品的中央,有一处代表海水泡沫的白色物质。制作人尼克告诉她,那是他的弟弟拉斯提的一小块骨灰。拉斯提生前热爱冲浪,后不幸意外身亡,尼克专门制作了这件纪念品。据尼克介绍,这家工作室专门负责为客户定制含有骨灰的纪念品,目前从全美两万多个殡仪馆接收订单。
生命宝石,是近年来在美国得到迅速推广的另一种新式纪念物。其制作工艺原理,是用极高的温度和压力,加速实现碳单质转化为晶石的自然地质过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一工艺主要用来制造人造钻石。如将相关工艺用于骨灰压制,得到的产品便是生命宝石。在美国,目前一件生命宝石的制作成本在两千五百至两万五千美元不等。香农了解到,生命晶石的制作需要提前预订。根据体积大小,制作时间一般在四个月甚至一年。一颗制作成功的生命宝石,会附有一份防伪证书,上边“标注着一个微刻在钻石上且已被录入全球钻石登记簿的编号”。如同每个人都是唯一的存在,每一颗生命宝石也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仅玲珑精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能够长久保存。香农还发现,选择生命宝石的顾客百分之八十是美国人,其他顾客来自加拿大和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
此外,一种名为“骨灰画像”的业务,也正在迅速发展。骨灰画像,顾名思义,即用骨灰创作逝者的肖像画。从事该项业务的青年艺术家表示,肖像画的绘制在笔法和风格上要求各有差别。最为重要的,是要体现出人物的独特个性。香农调查发现,每张肖像画的基准价在两百美元。“骨灰画像”的日渐流行,折射出美国人渴望拥有更独特的纪念方式。
随着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希望能够保存逝者生物属性的创意产品也在探索之中。比如,一些美国人在去世后,其指纹会被殡葬师提取下来,然后通过激光镌刻技术刻在冷却后的、五光十色的玻璃吊坠上。更有一些创业者,将目光投向了逝者的DNA双链。每一个人的DNA都是唯一的,保存住DNA无疑便保存下来逝者最为本质的部分。DNA被提炼出来,也会被保存在性质稳定、肉眼可见的基质上,在室温中长久储存。
特别吸引读者眼球的是,美国部分州还出台了一些法律,允许逝者可以在特定的地点撒散骨灰。逝者的亲属可选择将骨灰带到逝者生前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然后在合法的地点撒下部分骨灰。一位名叫罗德的受访者,便是这样处置其妻子雪莉以及雪莉父母的骨灰的。被撒散的骨灰,和大地永远融合在了一起。
除此以外,香农还绘声绘色地介绍了美国其他一些新奇的遗体或骨灰处置方式。如遗体堆肥、遗体碱性水解法、遗体冷冻葬、(骨灰)太空葬、(骨灰)圣烟葬……,无不体现出了美国民众在死亡最后一程安排上的独特追求。
最后,不同于20世纪主要由殡葬专业人士料理遗体,美国的葬礼出现了向工业化时代以前的家庭模式回归,逝者家属开始从殡葬专业人士的手中回收权利。香农发现,北加州是家庭自办葬礼的中心。不仅有专门的家庭葬礼指导人士,同时在各地还有家庭葬礼培训班。家庭自办葬礼联盟,甚至在美国各地也出现了。家庭葬礼鼓励家属触摸逝者的遗体,为逝者清洗穿衣,尽量没有遗憾地完满地送逝者最后一程。于是,一些独特的、充满个性化的告别形式出现了。比如,一些逝者在经过专门的技术处理后,被家属摆成生前喜欢的姿势,与前来悼念的亲属、朋友进行告别。家属之所以这样做,有的是基于逝者生前的遗愿,有的则是根据逝者生前的性格特点有意为之。在这场最后的、“浪漫”派对中,逝者成为了一名“无声无息”的主角。相关情节描写,对于中国人而言,无疑充满了“诡异”甚至惊悚的氛围,但却是在美国正发生的事实。此外,在很多美国墓园,香农还发现,美国人越来越喜欢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祭奠死者。
三、为何新世纪的美国葬礼充满“个性”?
如何理解21世纪以来,美国人殡葬习俗中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对此,香农表示自己无意进行全方位考察,但她也进行了很多值得重视的讨论。香农追溯了新世纪以来,美国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对美国人生死观念的影响。与此同时,在为期五年的调查中,对于每一位受访者,香农都会尽量问两个问题:“你想选择什么样的安葬方式?”“你认为死后世界是什么样的?”香农将美国近年来殡葬习俗的变化,与美国人对于个人、国家和宇宙的观念认知联系了起来。
在追寻美国历史上殡葬习俗发生变化的因素时,香农尤其强调重要历史节点的影响。正如南北战争中美国士兵的大量死亡,助推了防腐技术被应用于遗体维护,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美国的殡葬传统。2001年“9·11事件”的发生,则是形塑美国殡葬习俗的重大事件。在这场暴恐事件中,美国人从现场或电视中看到了双子塔的轰然倒塌以及遍地狼藉的遗体残肢和碎块。当然,还有很多人迄今尚未得到身份确认。在激烈的爆炸中,他们不幸“化成了血雾”。香农强调,美国人完整的遗体代表逝者本人的观念瞬间崩塌了。与此同时,遗体在葬礼中具有的情感慰藉作用也在逐渐消散。在美国人的心目中,遗体失去了“神圣性”,成为了一具具占用资源、需要处理掉的“空壳”。这次暴恐事件后,美国人开始直面遗体,观察它的细节,同时开始接受腐烂的发生。《识骨追踪》《刑事现场调查》以及《行尸走肉》等影视剧的大量涌现,就是当下美国消费文化的一种折射。与此同时,在万圣节等重要活动中,很多美国人将自己打扮成为僵尸的模样,以至乐此不疲。不难看出,“9·11事件”的发生,形塑了美国人的死亡观。
其次,气候危机和自然灾害也对美国的殡葬习俗同样造成了深刻影响。美国,是世界上各种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之一。二十一世纪以来,飓风、海啸、泥石流等大规模灾害不时发生。2005年的“卡特丽娜”飓风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奥尔良登陆,造成1863人死亡,数十万人流离失所(徐富海:《城市化生存:“卡特丽娜”飓风的应急和救助》,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1页)。不断发生的气候危机和自然灾害,让美国人的生态环保意识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看到了人为活动对自然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大自然正在对人类的报复。这反映在殡葬习俗中,便是人们对绿色殡葬的认可。香农不无调侃地写道,相对于美国民众对绿色殡葬的欢迎,美国政府和公墓经营者的反应则相对迟滞许多。
与此同时,美国人殡葬习俗的新变化,还与传统宗教观念的影响式微相关。香农指出,新世纪以来随着美国信仰宗教人数的减少,宗教对于人们的影响也在发生变化。这体现在遗体处理上,就是长期居于支配地位的宗教传统正在失去影响力。大多数宗教对各种葬礼,也不得不持开明的态度。关于灵魂是什么,“人们也不再以宗教的观点马首是瞻”。在新世纪反抗传统、质疑权威的文化趋势下,美国社会围绕殡葬生发出了“高度个人化的信仰”。在现实生活中,美国人越来越喜欢按照自己的个人想法行事。有些葬礼在他人看来,甚至有些“随他去”的玩闹性质。同是在这一过程中,那些跨行业进入殡葬领域、创办殡葬产品创意公司的创业者,无疑又成为了塑造死亡的“引领者”和“操刀手”。他们在一起,塑造着美国人的死亡。
此外,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也影响到了美国人对待殡葬的态度。现代临终关怀事业,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后迅速传到美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临终关怀服务已得到美国人的广泛认可,并被纳入联邦医疗保险。临终关怀原本是为罹患绝症的病人,提供医疗护理和情感关爱。后来,临终关怀服务扩展到了帮助弥留之人了解自己的选择,以及掌控那些可能会影响自己或家庭的重大决定。临终护理事业的发展,使得病人及家庭的决策权日益彰显,出现了临终护理的“家庭回归”。随着临终护理从医院和长期护理机构向家庭的转移,病人也能够积极参与策划身后的纪念活动。香农一针见血地指出,临终关怀事业在美国的发展强化了美国人的一个观点,即“在殡葬问题上,个人拥有选择权。”
最后,美国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导致美国殡葬习俗深刻变化的深层原因。在讨论这一问题时,香农将个人主义与美国人的“人观”联系在了一起。人观,即“人的观念”,是一个由人类学家莫斯提出的专业术语,主要用来讨论一个社会中的人如何看待个人与国家和宇宙之间的关系。人观是一个流动性的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人观也会发生改变。香农指出,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的人观认为,人的灵魂、个体都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这直接影响着二十一世纪以前美国人对待遗体和个人的态度。然而,在“9·11事件”等各种重大事件的影响下,美国人的人观发生了深刻改变。二十一世纪美国人的人观已不再是一个整体,而是可分的。这反映在人们对待逝者上,逝者的某一个部分或某一生物属性都可以代表其本人。也便如此,包含骨灰在内的各种纪念物才会在美国大行其道。香农指出,这种可分的人观,在很大程度上进一步又强化了美国个人主义的发展。从而,也在影响着当下美国人在“美国人是谁?”“身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等问题上产生疏离,在很多重要社会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香农的这一认识是深刻的,不仅可以很好地解释美国各种新奇殡葬习俗的出现,同时对于理解美国社会的其他现实问题也颇有助益。
在香农看来,遗容瞻仰、遗体防腐作为一种全国性的“仪式规范”,受到多数美国人的认可,这在深层次上体现着一种“国家-身体”的观念认同。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美国人传统的个人主义人观的变动,美国人的宇宙观也在发生着改变。香农指出,尽管美国人对传统宗教正在失去兴趣,但是美国人并未因此而变得更加世俗,而是对神秘主义的“灵性”充满好奇。“对鬼魂、转世和星尘的信仰,塑造了美国人的宇宙观”。与传统宗教的天国观念不同,鬼魂、转世和星尘的观念更多指向的是此在的世界。用香农的话说,这种新的宇宙观,指向的是“一种以共有的生态观为基础而形成的地球共同体”,而不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说的以国家为导向的“想象共同体”。在这种宇宙观影响下,美国的“公墓正在成为森林,整个国家都成了潜在的死亡景观,哪里都有可能是逝者的安息之所”。个人和生态地球之间的联系,成为了美国人思考死亡的核心议题。
对于美国殡葬习俗在二十一世纪日新月异的变化,香农并不想给出面面俱到的解释。但是,通过她诸多颇有见地的分析,依然能够让读者了解到这些变化发生的重要原因。即,拥有高度个人化信仰、尤其强调自我主体性的美国人,正在根据其个人信仰、性格、爱好等重新形塑死亡,同时也在赋予自己的生命以全新的意义。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译者将这本书翻译成了《我想这样被埋葬》。当然,尽管当下美国的殡葬习俗正在变得别具个性,但在形形色色的习俗背后,也体现着人类对生命意义追寻的共通之处。美国人在面对死亡上,无论是灵魂观,还是转世说,抑或是人死之后成为星尘永留世间,都反映出了人类对于生命永恒的一种执着追求。21世纪的美国人对生命永恒的追求,并没有改变。而这,恰恰是殡葬文化的本质所在。换句话说,尽管美国的殡葬习俗形式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来生,从来就不是虚无。
读罢全书,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对这样一本连作者本人都认为“古怪”的殡葬人类学著作,译者为何要不辞辛劳翻译成为中文?英文原版中各种新奇的专业术语,翻译起来实非易事!个中原因恐怕除了译者对死亡议题有浓厚兴趣外,可能还与其希望中国人能够对当代殡葬习俗的演变以及背后的生死问题多加关注和省思有关。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当前中国大陆地区的年死亡人口已然突破了一千万。按照一场丧事约有三十人参加计算,一年参加过丧葬活动的人口即多达三亿多人。在此种情形下,人们对于死亡和殡葬议题不可能不发生兴趣。在现实中,殡葬服务中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潮流。由此,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如何审视和思考死亡?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又应当如何安排好人生的最后一程?中国的殡葬习俗又在发生哪些显著变化?无疑都是有趣的思考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香农这本书被译成中文,也便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家装公司,本文标题:《马金生评《我喜欢这样被埋葬》丨来生并不是虚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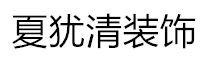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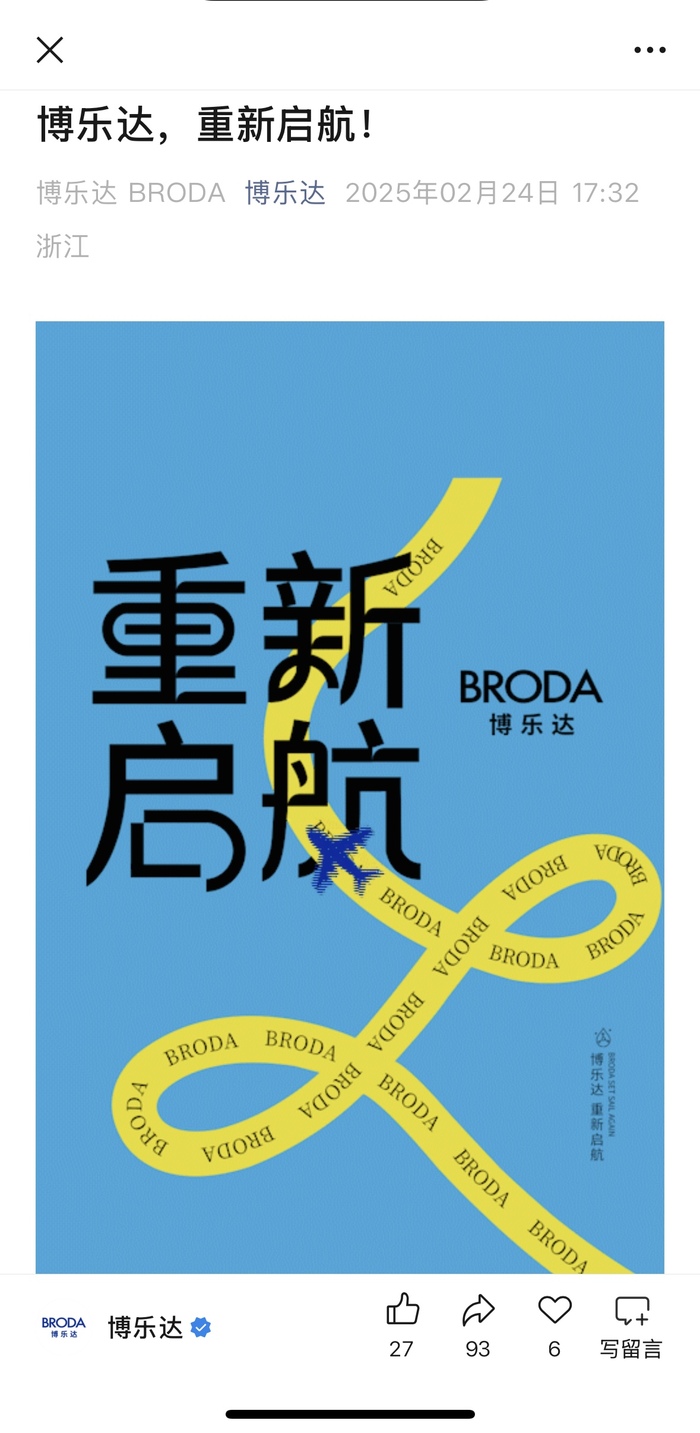
 京ICP备2025104030号-5
京ICP备2025104030号-5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